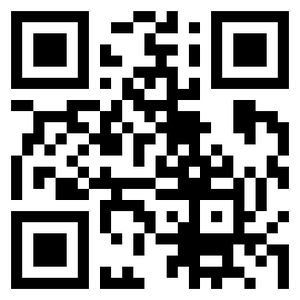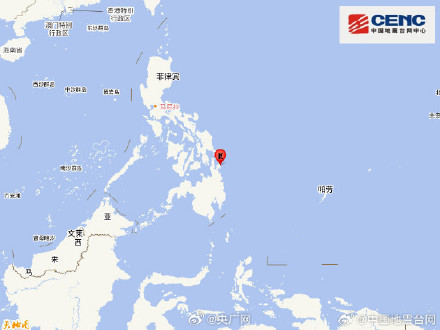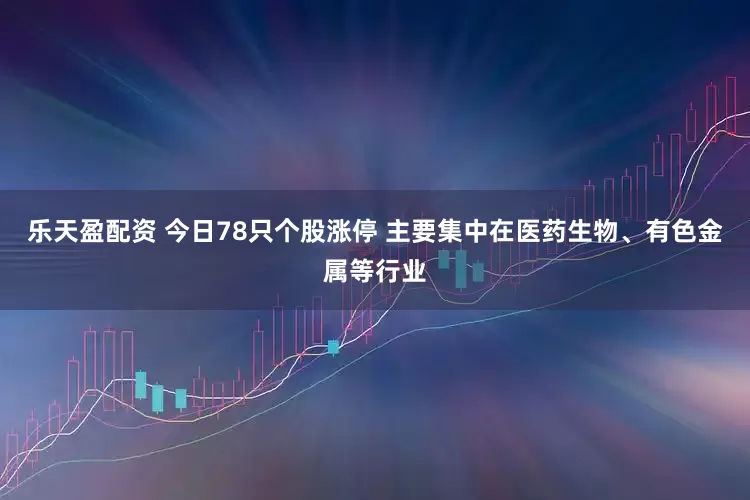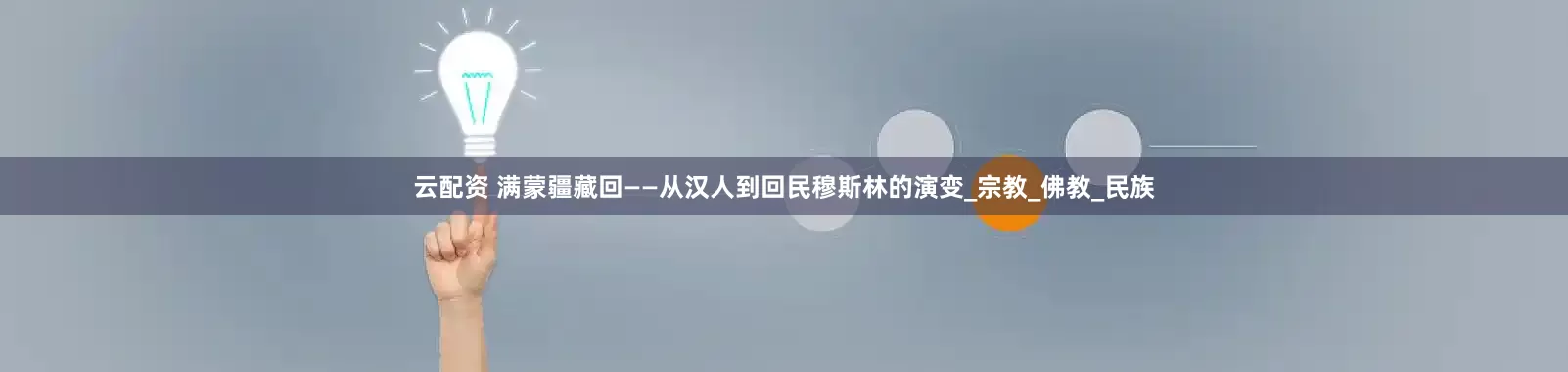
青藏高原的藏人逐渐从苯教信仰转变到佛教信仰云配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宗教的传播与发展,都需要结合本地民族的特点进行一定的变化。当然,民族和宗教的概念虽然不同,但是,在今天的学者将宗教与民族进行了一定的绑定,也就是所谓的文明理论。
文明是一个更加高维的概念,民族是现实基础。不同的民族为了团结起来,必须选择一定的意识形态。唐朝之后直到明朝的这段时间里,藏族人的雍仲本教和藏传佛教不断的融合——对抗。藏王倾向于哪一方,哪一方就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毕竟,宗教的传播途径中,走上层路线自上而下的推广,会有更好的效果。
底层的人们也会有自己的选择。青藏高原的宗教化趋势,总体上是佛教占优势。同时,也会有灭佛这样的事件发生。最终,经过一系列的融合,佛教终于在藏族人心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佛教也在西藏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轮回转世的体系。相较于苯教,佛教更有组织化和体系化。
到了清朝时期,青藏高原已经完成转向了佛教信仰。蒙古高原的游牧者也选择了皈依法王,为了更好的控制漠南漠北的游牧者。来自白山黑水的渔猎者进化成华夏大地的儒家皇帝之后,也向青藏高原的班禅和达赖抛出了橄榄枝。这也是如今清王朝宫殿居所中有大量藏族佛教形象的来源,佛教有不同的分支,汉人也早已经接触到佛教,并不算陌生。
展开剩余94%草原的蒙古人,雪域的藏人,东北的满人,华夏的汉人。对于佛教这个意识形态,都有了熟悉和了解。虽然分支不同,但总归还是一个宗教旗下的教友。无论,我们之间有再多的区别和差异。在佛教这个宗教基础之上,我们总归是有了一个比较勉强的联系点。陌生的也逐渐不再陌生。隔阂会存在,却趋向于了解和沟通。
就在明清之际,大西北的陌生人终于来了。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其实,我们本来不会陌生。其实,我们之间的文化底子和民族基因都是一个文明。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民族和宗教是一个后来的概念,无论其能否匹配明清的故事,却真实的发生在大西北塞外。
宗教发展到膨胀的地步,就会产生不同的派系。东正教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正教徒,同样的,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认为自己才是亚伯拉罕派系的正教徒。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流派有对应的概念,实际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的教派信徒。
民族受到地缘制约后,在语言和文化有了差异性。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成为上位概念,下面有许多的分支民族。分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在明清之际的大西北。从宗教上有了分化趋势的人,最终在共和国建国之前,形成了独特的民族。
如今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中,回族的人口基数较多,与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与的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一致。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民族,因为,大西北的汉人穆斯林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但是,我们很多人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报告,北京市有二十多万汉人穆斯林,市内的清真寺数量达到70个以上。鉴于民族和宗教政策的特点,如今的汉人穆斯林数量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除了北京,在我国的各个城市都有一定数量的汉人穆斯林。除了历史上的汉人穆斯林传统聚居区,越来越多的地区也有了汉人穆斯林。
在2023年之前,中国还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便被印度超过之后,也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穆斯林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宗教群体,预计到下一个世纪的时候,伊斯兰的信徒很可能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宗教都多。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仍然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非洲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化石燃料,这些国家也构成了蓬勃发展的中国商品、技术和劳动力市场。作为交换,中国向穆斯林国家提供军事装备和基础设施物流。
中伊合作还经常受到共同利益的推动,即抵制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随着中国及其穆斯林客户和合作伙伴继续发展壮大,国际上的合作和相互依赖,将在可预见的将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
随着地缘政治焦点越来越多地转向亚洲,了解世界大事的观察家,应该注意中国与全球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的历史交往,在塑造世界历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几个世纪以来,沿着连接西亚和东亚的地区,这些文明之间进行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传递了商品和思想的双向交易,我国当前作为世界大国的抱负,以及对物质资源、外国市场和在全球战略地区更大影响力的追求,让人们回想起一段辉煌的过去。
这些抱负激励着中国向中亚和中亚以外的穆斯林国家进行陆上延伸。中国和穆斯林世界在历史上还进行过海上贸易,涵盖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如今双方在这些地区再次进行互动。这些陆上和海上通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该倡议寻求在商业、政治和文化交易方面与全球一半的国家建立联系。
公元618年开始,唐朝以包容开放的大国姿态,将汉人的威仪和文明传播得更远。当时的世界舞台,长安是绝对的聚光点。根据史料的记载,正是在唐朝之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来到了大唐长安城。长安城中的外国穆斯林群体,逐渐在大唐生活下来。他们成为了大唐的子民,这些穆斯林也成为了今天穆斯林的先祖。
在穆斯林第一次踏足我国之后的一千年里,他们的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到中国历史、中国以外伊斯兰教传统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如今,中国穆斯林是一个内部多样化的群体,在五十五个得到承认的少数民族中占十个,与其他少数民族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一起生活。
除了伊斯兰教派之间的松散联系外,这些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很多方面都与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的非穆斯林民族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在地理、民族、语言、经济、教育以及宗派和血缘关系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更复杂的是,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内部多样性,以其宗教虔诚程度,而非世俗性和“中国化”,融入主流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程度为特征。
不幸的是,二元性经常导致政策制定者和一些学者,过度简化中国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冲突,要么是和谐。事实上,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对穆斯林社区既产生了向心的作用力,也产生了离心的作用力。一些人抵制失去自治和独特性,而另一些人则接受包容和综合;这两种反应都促成了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独特解释。
尽管中国的伊斯兰教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口音,但全世界约二十亿穆斯林所信仰的宗教传统在中国是得到认可的。中国穆斯林信仰真主安拉,并确信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和使者。他们每天面向圣城麦加祈祷五次。他们实践伊斯兰教的施舍、斋月,甚至去朝觐麦加。
中国穆斯林会遵守《古兰经》和先知教义规定的同样的饮食法。他们为自己的清洁和节制传统而自豪,并高度重视在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的婚姻和家庭价值观。傲慢和偏见是人类的通病,外国人会认为中国穆斯林有自己的中国传统特色。中国人也会认为中国穆斯林是一个有自己宗教特点的群体,他们就像深陷于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一样。
中国穆斯林群体有两个特别大的分支云配资,分别是西域的新疆维吾尔人和大西北的汉人穆斯林。从民族感情上来看,大西北的汉人穆斯林和汉人有着更多的联系。而且,汉人穆斯林更加温和。今天,我们先来了解汉人穆斯林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唐朝皇帝被自己刚刚看到的景象吓了一跳,惊醒过来。在梦中,宫殿的椽子和柱子在摇晃,预示着死亡和毁灭的邪恶力量。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一个外国人——穿着绿色衣服,戴着头巾,拥有镇压怪物和避免即将到来的厄运的力量。“这个陌生人是谁?这个可怕噩梦的含义是什么?”皇帝在醒来后立即召集大臣提出一个问题。其中一位部长回答说:“一个邪恶势力威胁要摧毁你的王国。然而,西方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圣人,他可以用祈祷来驱除恶魔。只有他才能拯救帝国。你必须找到这个人,并立即把他带到中国,以确保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皇帝随即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西方寻找这位圣人。他们穿越了帝国的边界,越过遥远的昆仑山脉,深入蛮族地区的心脏地带。最终到达了一个沙漠绿洲,在那里,这位伟大的圣人以简单的方式统治着他的子民。圣人接待了中国代表团。他们向他讲述了皇帝的梦想,并恳求他到自己的国家。但他忙于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他任命了一个由他的追随者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带来和平福音。皇帝接待了外国使者,为了感谢,允许他们留下来,给他们土地,并允许他们娶中国新娘,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后代。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反复讲述这个故事,以解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起源。这个故事的核心元素——先知穆罕默德派遣的使团受到皇帝的欢迎,阿拉伯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留在中国,成为今天中国穆斯林人口的祖先。
一个对特定人群具有特殊意义、代代相传、表达他们最深信不疑的信仰、价值观和集体愿望的故事,是神话的恰当定义。事实的历史性从未成为神话价值的关键。正如宗教历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解释的那样,神话的价值在于它把人与神联系起来,让他们在世俗存在之外。
神话叙事中描述的事件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讲述神话就是宣布事情的起源。一旦讲述,也就是揭示出来,神话就变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它确立了绝对真理。”如上文所述,起源神话把人们带到了他们的历史之外,并允许他们把自己想象为神圣现实的一部分,赋予他们的存在终极意义。叙事中的历史或伪史,细节是已知世界的参考点,将神圣与世俗联系起来。因此,神话和历史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尽管有时是相互关联的。
生活在重视家谱的文化和社会中,家庭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前,中国的穆斯林自然希望培养一种归属感,以及社区的合法性。他们试图理解多样化的混合遗产,并以神话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声称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遗产,汉人穆斯林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宗教叙述和一个崇高的民族身份。
汉人穆斯林扎根于中国,一个生活在占压倒性多数的非穆斯林人口中的少数民族。然而,在他们的宗教愿望和集体文化记忆中,汉人穆斯林与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根源相连,在精神上与先知和他的同伴相连。
最早的穆斯林与中华帝国的接触,发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更古老的大背景下。早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之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文明之一。黄河流域,就像埃及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一样,提供了支持广泛农业、经济盈余、有记录的史前时期大型定居人口中心增长,以及后来古代城市和国家所必需的自然资源。
冲积而成的摇篮中的人们,创造了平行的人类文明基础,当他们扩展到超出其地理界限时,继续传播其文化和领土主张。考古和史料证实,当代全球化的现象,只是史前时期开始的一个过程的最新阶段,文化及产品的交流已经持续了数千年。
到公元前2世纪,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中国已经将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向西扩张到中亚地区。汉朝使臣张骞前往该地区,建立中国的商业和外交关系。中国的商品沿着半游牧的中亚人建立的路线,穿过欧亚大草原和沙漠,最终到达古代地中海的市场。在这些市场上,消费者最渴望的商品之一就是丝绸,当时养蚕业是中国垄断的,因此,东西方贸易路线在历史上被称为“丝绸之路”。尽管它从来不是单一的道路,许多种类的商品沿着它传播。
商业交通也不是单向的。中国从中亚进口马匹和奢侈品,例如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古墓中发现的罗马玻璃。在汉朝和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连接两国的陆上贸易路线,即使在两国衰落并最终灭亡后,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因此,在伊斯兰教兴起很久之前,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就已经为商业和文化交流搭起了历史舞台。
同样,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各民族就已经与现有的陆上和海上贸易网络建立了联系。大马士革是丝绸之路西端的主要贸易站之一,货物就是从那里运往和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从叙利亚到也门的商队沿着一条贸易路线旅行,这条路线经过阿拉伯半岛西部定居点,其中包括麦地那和麦加等城市,返程时带着香料和麝香、乳香和琥珀。
因此,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经知道中国的存在。波斯和阿拉伯的航海商人早在伊斯兰教时期之前,至少两个世纪就冒险从海湾进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几乎可以肯定,来自海湾波斯港口的船只,在公元六世纪末或七世纪初,就到达了中国。因此可以想象,一些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拉伯人,可能在同一时间航行到中国。印度洋上的贸易路线通过狭窄的马六甲海峡相连,构成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另一种将货物、人员和文化,从中国和广阔的印度洋地区运送到非洲东海岸的途径。
在公元605年,隋朝开展了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修大运河,将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与内陆中部的河流和航道连接起来,直到帝国的首都长安。连接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后,进一步促进了帝国内部的商品和人员流动。与其他无数文化和宗教,包括佛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和景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是通过贸易传播到中国的,贸易也是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的主要途径。
无论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都是沿着陆路和海路,在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之前很久,就沿着贸易路线来到中国的。当他们到达中国时,会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的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发现其他外国商人的飞地,他们会与这些人进行交易和互动。
唐朝向西扩张进入中亚,重振丝绸之路贸易,伴随着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和中国精英对异国情调文化的兴趣。唐朝的领土扩张既是通过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结果,因此,该政权热衷于领土扩张,尽管官僚机构的儒家意识形态蔑视商业,对外国人持蔑视和怀疑态度。学者官员认为外国文化本质上低人一等,并且对中国儒家文明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然而,儒家文人对儒家文明的优越性,缓解了这些疑虑,这助长了他们的期望,即外国人自然会被中国文化的美德所吸引,放弃自己的野蛮方式,接受文化,即文明化。
早在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和贸易,就由基于这种儒家意识形态世界观的严格法规所规范,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来自帝国周边国家和国家的外国人,被认为在文化上处于劣势。为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必须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和宗主权,象征性的仪式是在皇帝面前磕头。他们还会用贵重商品、金银等贡品来尊崇皇帝。作为回报,皇帝会赠送同等甚至更大价值的礼物,根据关系和交流的重要性而定。这种朝贡制度一直统治着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直到清朝结束。
在维护儒家的中国文化至高无上观念的同时,也在官方层面规避了贸易的污名化。虽然商业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经济现实,但儒家学说将农业和手工艺视为谋生手段,对商人持蔑视态度,认为他们是社会中最低贱的阶层,不劳而获的中间商,他们什么也不生产,只是从他人的劳动和创造力中榨取财富。儒家对蛮族文化和贸易的双重偏见,给包括穆斯林在内的旅居外国人蒙上了阴影,在伊斯兰教传入和发展过程中,这给他们的接受带来了反复挑战。
贸易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但并非唯一途径。纵观历史,贸易往往与外交携手并进。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外交朝贡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事实上,汉朝官员张骞出使西域的初衷就是建立外交关系,以促进贸易。随后的朝代延续了这一政策,并有所发展。唐朝的势力范围比前朝更向西扩展,导致陆上欧亚大陆商业、政治和文化交流的繁荣。
唐朝的官方史书详细记录了朝廷在长安欢迎的许多进贡政治使团。邻国和汗国定期向唐朝派遣使节,包括东部的朝鲜和日本;西部的克什米尔、尼泊尔、西藏、库车、喀什和于阗;南部的越南和占婆。在北方,唐朝与庞大而强大的维吾尔汗国保持特殊联盟,他们在中国和各种游牧突厥语、原始蒙古和契丹部落之间提供缓冲。
当时已知世界的更远国家也派遣使团,包括拜占庭安条克大牧首和波斯萨珊帝国,他们的使节访问了太宗皇帝。公元七世纪,在亚洲大陆的两端,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和唐朝几乎同时出现。李渊于公元618年,在前隋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王朝,遵循中国古代帝王传统。另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与追随者从麦加来到麦地那,建立了新的神权国家。
当新兴的麦地那伊斯兰国仍在为生存而与麦加的非伊斯兰信徒斗争时,高祖的儿子李世民杀死了两个兄弟,然后继承了父亲的皇位,开启了唐太宗的统治。他的统治开启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其标志是领土扩张、经济繁荣以及基于外国影响的世界文化的繁荣。正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唐帝国发展了宗主朝贡体系,并保持了作为其他帝国认为有必要派遣外交使团的地缘政治大国的地位。因此,在公元七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帝国,继续与中国发展各自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这两个王朝晚期一直争夺对中东的控制权,现在它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共同威胁。
这个威胁来自它们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兴起。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公元 628 年至 632 年之间,先知穆罕默德派使者前往阿拉伯半岛周边的国家,传达邀请其统治者接受伊斯兰教,并服从其权威的讯息。这些邀请被拜占庭、埃及、波斯和也门的领导人断然拒绝,最终穆斯林军队征服了这四个国家。虽然先知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使阿拉伯半岛的大多数部落皈依伊斯兰教,但直到他于公元 632 年去世后,该宗教及其政治才真正开始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以外。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在穆罕默德的前四个继任哈里发的领导下,穆斯林国家在传播伊斯兰教和扩大领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对阿拉伯半岛反叛部落的里达战争中获胜后,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开始对伊拉克的萨珊军队和黎凡特的拜占庭军队发动军事行动。在哈里发·奥马尔的领导下,穆斯林军队在公元636年的雅尔穆克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拜占庭人,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同年,穆斯林在卡迪西亚战役中击败了一支萨珊军队,导致伊拉克被征服。公元642年,穆斯林在纳哈万德战役中的胜利给了萨珊波斯致命一击,导致沙·亚兹德格尔德三世出逃,萨珊波斯被伊斯兰教征服。
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都曾与唐朝保持朝贡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被伊斯兰征服所打断。651年,逃往中亚的佩罗兹三世,在唐朝宫廷寻求庇护,甚至请求高宗皇帝帮助他重建萨珊王朝的统治。在唐朝的帮助下,佩罗兹三世几次试图在波斯恢复权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定居中国,在那里得到了贵族地位,直到因不明疾病去世。他的后代留在中国,并被纳入唐朝贵族。
同样在公元651年,在高宗统治期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据说也派了一个使团前往中国。唐朝与萨珊帝国结盟,并与拜占庭帝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两个帝国都发动了与穆斯林国家的战争。然而,出于现实政治的实用主义,认识到新兴的伊斯兰哈里发国的实力,唐朝政权两面下注,欢迎来自这个国家的外交使团,《大唐西域记》将这个国家称为怛逻斯,怛逻斯是早期阿拉伯穆斯林政权的统称。
对哈里发使团前往长安的描述,有时与中国穆斯林起源神话的其他版本混为一谈。穆斯林击败了萨珊王朝,萨珊王朝曾统治着一个深入中亚腹地的庞大帝国,这也为伊斯兰征服和扩张到该地区开辟了道路。在赢得纳哈万德战役后的十年内,穆斯林将他们的行动扩展到锡斯坦和呼罗珊地区。在 651 年,征服呼罗珊城市梅尔夫后,伊斯兰统治已经到达阿姆河。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穆斯林军队横跨阿姆河,横扫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富饶的平原。
在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征服中亚的行动仍在继续,该王朝将古代丝绸之路中心,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纳入其领土。穆斯林军队在该地区取得了初步的军事胜利,当地波斯和突厥居民的叛乱,阻碍了穆斯林对突厥斯坦的平定。其中一些居民至少在名义上仍然忠于前萨珊统治者,并呼吁唐朝提供支持。正是这种呼吁导致唐朝试图支持被废黜的萨珊王子佩罗兹三世,但以失败告终。新建立的倭马亚王朝,忙于所谓的第二次内乱,巩固其对伊拉克和阿拉伯地区的控制,镇压对其统治的叛乱挑战,使其无法全力沿东部边境扩张。
穆斯林军队甚至一度从呼罗珊撤退。然而,倭马亚王朝在公元八世纪初,重新站稳脚跟后,夺取中亚稳固控制权的战役开始展开。领导这次军事行动的是著名的倭马亚王朝将军库泰巴·伊本·穆萨。到公元 713 年,库泰巴已经率领他的军队穿过中亚,到达唐朝边境。伊斯兰学者和历史学家塔巴里写道,库泰巴甚至穿越了靠近喀什的唐朝领土,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了后来历史学家的质疑。
到了公元751年的7月,阿拔斯军队与唐朝军队在怛逻斯河流域相遇。阿拔斯一方有西藏军队助阵,而三分之二的唐朝军队,由来自葛逻禄部落联盟的雇佣军组成,这些游牧者来自中亚西部。
据估计,双方军队人数相差悬殊,达到数十万之多。战斗持续了数天。然而,这种僵局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事实证明,葛逻禄雇佣军是不可信赖的盟友,他们在战斗中叛变。唐军被阿拔斯军队和葛逻禄战士围攻,很快被击溃。高仙芝将军只身逃走,带走几千名士兵。穆斯林军队短暂追击,但被唐军东部增援部队击退。
最终,阿拔斯王朝在怛逻斯之战中战胜了唐朝,但领土现状基本上得到了维持。由于这场胜利,哈里发无法取得任何优势,也从未进一步向东推进。也许这就是怛逻斯之战在当时的伊斯兰史学中,没有得到突出体现的原因,在后来的穆斯林来源以及唐朝的官方中国历史中都有记载。阿拔斯胜利和唐朝失败的直接影响可能并不明显。
传说穆斯林军队俘虏了一些中国工匠,包括一些知道如何制造纸张的工匠。这些工匠被带到撒马尔罕,他们在那里传授了他们的手艺,从而将造纸技术传播到伊斯兰世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对中亚阿姆河地区的影响确立。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停止。
一件不同寻常的叛乱,帮助改善了中国和穆斯林帝国之间的关系。公元755年,也就是怛逻斯之战结束仅四年后,唐朝经历了内乱,对其生存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是唐玄宗统治的最后一年,一位中亚血统的唐朝将军安禄山煽动叛乱。公元756年初,安禄山占领了洛阳,即唐朝的东都,并宣布自己为大燕皇帝。安禄山将目光投向了西都长安。当叛军准备入侵时,唐玄宗和他的朝廷逃离了首都,在今天的四川省避难。就在那里,唐玄宗退位,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后者在今天的宁夏省灵武登基为肃宗。
决心夺回长安的肃宗皇帝,从突厥汗国补充了军队。此外,为了获得援助,皇帝还请求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提供军事援助。曼苏尔派大约四千名雇佣兵和突厥人并肩作战。大燕朝廷内部爆发阴谋内乱,这个叛乱王朝变得越来越脆弱。公元 757 年,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和他的两名大臣刺杀。不久之后,唐朝联军将叛军驱逐出长安,不久又夺回了洛阳。
阿拔斯哈里发帮助击败了叛军,与唐朝帝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公元 758 年,阿拔斯哈里发的外交使团受到长安唐朝朝廷的欢迎。肃宗皇帝还奖赏了为他而战的阿拉伯穆斯林士兵,邀请他们留在中国,并给他们分配土地,允许他们娶中国新娘。
唐朝时期的繁荣和动荡,为西亚穆斯林的到来,提供了绝佳的时机。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来到了中国,跨海而来的穆斯林群体主要居住在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从丝绸之路而来的穆斯林,则大多生活在长安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城的穆斯林群体势力越来越强大。最终,整个大西北地区的人们,开始了解这个有些神秘而晦涩的宗教。
唐朝末年,落第的考生黄巢留下了大气磅礴的诗句。为腐朽的唐王朝的崩塌加上了一根稻草,值得注意的是,黄巢起义辗转南北数千里。唐末的广州城中有大量的穆斯林群体,黄巢有纯粹的儒家观念,对穆斯林势力没有什么好感。冲天香阵透长安之前,就在广州屠透了穆斯林。在此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势力受到巨大打击,我国的汉人穆斯林聚居区以大西北为主。
宋元时期,以农耕为主的大陆文明开始侧重于海洋贸易。无论是孱弱的宋朝皇帝还是霸气的蒙元可汗,他们都为国家财政中增加了海洋贸易的比重。在这几百年的发展中,有些经商传统的穆斯林有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到了元朝中后期,可汗们更加看重财政情况,热衷于商贾之道的色目人扶摇直上。穆斯林势力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空间。
明朝的皇帝们除了早期还有扩地之心,后面的守成之主普遍都以更加内敛的姿态驾驭天下。明朝的海禁政策阻碍了外来穆斯林,但是,已经在大西北盘踞数百年的汉人穆斯林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明王朝推崇儒家思想,明朝的士大夫也有很大的信心。
所以,明朝时期的汉人穆斯林有了稳定不受影响的环境,得以继续巩固自己的文化认同。而且,蒙古人的威胁贯穿明王朝始终。后来者的东北女真人更是成为心腹大患,明朝的关注重点始终都在北方和东北方。西北方的穆斯林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状态,既没有影响存续的动乱,也不需要明朝皇帝重点关注。
明清之变的时候,汉人皇帝、蒙古大汉、女真国王三方势力互相制衡斗争。大西北的汉人穆斯林也在继续进化,逐渐产生了新的想法。后来,随着民国和共和国的更迭,汉人穆斯林终于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回族。
随着汉人穆斯林的势力崛起云配资,西北方的维吾尔穆斯林也逐渐走进汉人皇帝的视野中,早在很久之前,蒙古人就已经知道西域的这些穆斯林了。
发布于:浙江省德旺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